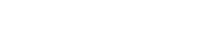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叶光庭
认识陈桥驿先生是我一生的幸运。
上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教书,可是我在中文系,他在地理系,互不相识。1957年我被错划右派,遭到批斗,陈先生曾受校里指派,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这是他初次“认识”我。我当时拒绝认罪,据理抗辩,他大概还有一点印象。
1958年秋,我被下放回乡监督劳动;1965年回校,文革时被安排在教材科,当个蜡纸刻写员。四人帮被打倒后,到了1978年,政治形势比较缓和了(虽然中央对错划右派还没有改正),我被陈先生调到地理系。
陈桥驿先生是为了急需找人翻译外国地理(这是国务院交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硬任务)才调我到地理系的。他有个堂弟是我在教材科的同事,通过这位堂弟,陈先生知道我懂英语,就到教材科来调我了。
陈先生把我调过去之后,又来调教材科另一个右派——吕以春,准备培养他作为学术研究助手。
我们都戴着右派“桂冠”, 在人们眼里,是些像麻风病人那样的不可接触者。文革时,陈先生本人就戴过“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挨斗。他不顾人们的闲言碎语,大胆搜罗我们这些右派,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可是他有一股倔劲,同时也是出于正义感,同情我们的冤屈,就毅然不顾一切地把我们调去了。
我们一到地理系,陈先生按照我们各自的所长,一件接一件地给我们分派工作。陈先生与国外学术界联系密切,书来信往,十分繁忙,我几乎成了他的“英文秘书”,不过我的主要工作还是译书。陈先生和出版界也有许多联系,常有出版社约他主编某类书籍,他就在系里找些有关专业的教师,组织他们来编写。不像有些名教授只关心个人的学术研究,他还特别关心系里年轻教师的发展。他把我们抓得很紧,有时一件工作尚未结束,另一件工作又分派下来了。
到地理系不久,陈先生就要我和吕以春编写一本介绍西湖风景名胜的书。我当时还不知道陈先生的良苦用心,只是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样需要专业知识、编写经验和水平的工作。其实陈先生对我们的经济困难早已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了,他是想帮我们弄点稿费,添补不足。这是很久以后他才告诉我的。书成之后,于1982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西湖漫话》,这是我们到地理系后出的第一本书。这本关于杭州西湖的书,却远在北方出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一位学术界朋友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社长,他就利用这点关系,替我们作“稻粱谋”了。
《西湖漫话》的出版,多少提高了我的信心,可是我终究是文科出身,对地理专业一窍不通,而且经历了20年来沦为贱民的悲惨命运,自然加重了自卑感,削弱了自信心。虽然专业不对口,我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但陈先生分派给我的任务,却愈来愈难,也愈来愈重。他给我安排的翻译工作,有些是专业性很强的,例如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R. Hartshorne)的名著《地理学的性质》和著名汉学家施坚雅(W. G. Skinner)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对这些工作,开始时我都不敢接受,感到远非我力所能胜。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陈先生总是鼓励我,帮助我,使我克服畏难情绪,完成工作,而且书也出版了,因此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陈先生是终身教授,我从地理系退休后,他保持仍然同我来往,介绍我做些工作。他说,退休后无所事事,不但内心空虚无聊,对健康也不利。他这些心里话,流露出对我的关心。我没有完全虚度此生,多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是应该感谢陈先生的。
在我出版过的书中,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水经注》的今译。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水经注》研究,是国内的郦学泰斗;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关于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各出版社相继出版各种古籍今译的图书。陈先生也希望能把《水经注》译成白话文,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但他本人有更重要的研究课题,腾不出时间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经过长期考虑,他终于选定了我。我过去接触的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国学根底很浅,觉得这样艰巨的任务,是超乎我的能力的,因此一再婉辞。陈先生善于用人,也善于挖掘人的潜力;他相信只要调动我的积极性,我还是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他一再鼓励我,自己也译了一卷作为示范。他对我的信任和器重,使我感动,觉得不能再执意推辞了,更不应辜负他的一番盛意。我凭借词典试读了几卷,有些难点向他请教之后也解决了,终于鼓起勇气,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不过我觉得工作量太大,希望找人合作,遇到困难也有人商量;陈先生也同意了。我找了两位合作者,出了第一个译本。此书在国内和台湾先后共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最后也是最完善的一个,是台湾三民出版社出的《新译水经注》,但由于各种原因,两位合作者先后相继退出了。
《新译水经注》虽然以“新译”为书名,但“译”在书中所占的分量,是远远不及陈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的。书中的大量注释,有许多涉及极其艰深古奥的典籍,一般人是极少猎涉过的。没有广博精深的学养,很难查出这些需要加注的典故、名物、职官,以及人名和中外古地名等等的出处。还有“研析”,当然也是陈先生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在这本书中,竟与学术界泰斗陈先生一同列名,既感到荣幸,也感到惶恐和惭愧。
2007年,我迁到浙大西溪校区启真名苑,和陈先生同住一个小区,往来方便了,有时也去看看他,一谈便是几个小时。往日陈先生有事来找我,总是匆匆而来,交代了几句,就匆匆而去,真是惜阴如金;今天他毕竟年事已高,劳苦工作了一生,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再像先前那样紧张,年年出书,月月发表论文了。陈先生很健谈,听他忆昔谈今,觉得趣味盎然。但我素性沉默寡言,所以当“听众”的时候居多。陈先生的记忆力特强,久远的往事,听他娓娓讲来,仿佛如在眼前。他谈到年青时出于爱国热情,曾参加远征军,给美军当翻译官。开始时听力不够好,常常要“I beg your pardon!”半个月后就好了。可见他学习能力极强,进步神速。我非常羡慕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他能出国讲学,也是这时打下的口语基础吧。回想自己,学生时代我所受的外语教育,专重文学而不重口语,日后又没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所以听力很差,讲英语也结结巴巴。我的英语只是“书房英语”,阅读和写作勉强还能应付一点,可是和外国人打交道就完全不行了。
陈先生的记忆力是祖父给他培养出来的。小时祖父要他背书,起先是背唐诗,以后背四书五经,日久遂成习惯。他背过英文辞典,背过英文小说。他说到莫泊桑的“The Necklace”, 安徒生的“The Match Girl”时,就大段大段地背出来,使我不胜惊异。我说他在记忆力方面是天才,但他说这是训练出来的。我确实读过些科普文章,说人的大脑如果开发出来,其潜力是惊人的。我想这恐怕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吧,真正要做到脑力最大可能的开发,至少总该有特殊的条件吧。古人读书都注重背诵,但很少人能训练出陈先生这样的记忆力。至于陈寅恪、钱钟书这样记忆力超人的大学者,几百年也没有几个。我对朋友们提到陈先生这样超强的记忆力,都说从来也没有见过。
陈先生思维敏捷,写作速度也是惊人的。他曾说年青时一晚上可写一万几千字;80岁后,还能每月发表一篇论文,每年出几本书。说他“著作等身”,绝非夸张之词。
12月10日是陈先生九十华诞,我写此文,既表示我个人对陈先生的感谢和敬仰,同时也表示对他九十华诞的祝福。
《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11月09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