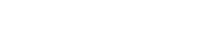首先得承认自己“做不好什么”,才能明晰“我能做什么”。顺应这种天性就是道,根据道进行修炼就是教。原来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自己,多年的“折腾”居然就是认识和寻找自己。
马一浮先生在《浙大校歌》中写道:“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在学术之路上,把握了“求是”和“启真”,就能“登堂”而“入室”。然而,“登堂”仍然有前提,那就是“寻路”。连“路”都找不到,何谈“登堂入室”?竺可桢老校长就很关心“寻路”:“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因此,每个浙大人都要面对竺、马二老的“学术三题”:寻路、登堂、入室。
我的问题是,尽管“登堂”多年,却迟迟“入不了室”。我是一个文科生,但从本科开始,就对定量研究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硕士论文把此法前前后后用了一遍,博士一年级还在持续旁听定量课程。多年来也发表了几篇论文,拿了一个省课题,但就是“找不到感觉”,离“入室”还远得很。机缘巧合的是,“启真杯”让我开始反思“寻路”问题。我读博的第一篇论文《寻根主义》(与导师邵培仁教授合写),就获得了首届“启真杯”“浙大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提名奖”。它给我的刺激在于,我从未写过这样的内容(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与研习多年的定量研究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含金量不低,这是本硕博所有年级和文理工农医所有学科一起评的。而能够入围,大概是因为这篇论文被一份cssci期刊列为“2013新闻传播十大观点”之首。确切地说,我和导师的论文观点,代表浙大排在第一,排在后面的有人大、中传、清华、暨南大学等教授,都是本学界的大牛。
我很疑惑:为什么定量研究做了那么多年,只能出几篇不痛不痒的文章?而第一次写中国古代思想,一下就能登大雅之堂?当然,首先是因为有“牛”导师邵培仁教授的指导,他希望我以古代思想为方向。如果说写第一篇论文是“焦头烂额”,那么写第二篇已“找到节奏”,写第三篇则是“渐入佳境”了。但如果换成了定量研究论文会怎么样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一次智力测验(旁听《高级心理测量》课时自测)。测完我恍然大悟:我在计算推理能力上的得分很一般,但在几个与人文相关的方面得分很高,如知识面、抽象概括能力、对实际知识的理解与判断能力、对词语的表达能力、对情境的理解和判断能力等。这意味着我一直在事倍功半地做研究,因为用的是自己最弱的能力。那为什么我还能坚持那么多年呢?或许原因有三:第一,定量研究方法很新、很“前卫”,我“入行”又很早,自觉抢占了先机;第二,我高考数学考了126分(居然还是文科班里最高),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现在想来应该是题海战术的结果;第三,这是最重要的,数学往往是“聪明”与否的指标,我很不愿意承认自己数学差,因为这无异于承认自己“笨”。
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偏材”,有“笨”的一面,也有“聪明”的一面,我应该从“社科”转向“人文”。也许这个决定是对的:从高中到本科再到硕士,我几乎没有拿过什么奖,印象中只拿过一次“院级优秀实习生”;但是,自从转向人文(特别是先秦传播思想)以后,我如同“被打了鸡血”一般。读博四年,我疯狂买书(买了1000多本),记了1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发表了26篇论文,其中12篇cssci(近23万字),4篇一级,1篇权威(《新闻与传播研究》,2.2万字,封面首推、当期首篇);拿了2次国家奖学金、2次三好研究生、3次优秀研究生;获得浙大“学生十大学术新成果提名奖”、浙大“争创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优秀博士助学金;即将跟导师合作出版30万字的专著;以学生身份担任学术期刊《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主办)的编委。我还惊奇地发现,以前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很差,但自从会读会写了以后,也变得会“说”了。我受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的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文化讲堂”第258期、“中华文化与传播大讲坛”第一期主讲;受浙大校友会邀请,在“启真”读书会上主读《论语》;受浙大博士生会邀请,担任“博士生青年说”第一期主讲等等。
此时我才感到,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多么重要。而认识自己何其困难!因为首先得承认自己“做不好什么”,才能明晰“我能做什么”。《中庸》一语道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当我读到这里时惊呆了,因为它说,上天赋予的就是天性,顺应这种天性就是道,根据道进行修炼就是教。原来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自己,多年的“折腾”居然就是认识和寻找自己。恰如《周易·小畜》所言:“复自道,何其咎?吉!”令我感慨的是,我现在所做的事,竟是童年时就喜欢的。小学时,我经常和几个同学畅谈历史故事,特别喜欢先秦历史,但初中以后的近二十年里,除了将其当作考试内容以外,就再也没有“重温”过。直到我的导师“命题作文”“启真杯”又强烈刺激,才使我重新找回了童年的兴趣。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贴切:“最崇高的精神力量,在今后的生活中对身心最有益的感受,莫过于某种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童年时代从故乡故居保留下来的回忆。”
现在,面对竺老校长的“寻路”之问,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到浙大来,认识自己;毕业以后,成为自己。也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更好地“登堂入室”,即马老先生说的“启尔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