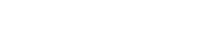敦煌离我们很远,但敦煌学却在浙江。自100多年前莫高窟藏经洞内数万卷古代文献被发现以来,浙江学者一直在追踪这一人类文明遗产,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世界的关注,还为敦煌学研究探索一条路径
今天,敦煌学已成为浙江大学本科生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这学期,敦煌学选修课原来只安排1个班,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改成2个班,听课的学生达到361位,即使这样,本学期仍有184位希望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未能选上。
学生们何以如此钟情敦煌学?浙大校务部教学科的刘理老师说:“这一方面是敦煌学本身有丰富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授课教师知识和授课艺术的肯定。”确实,浙江敦煌学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影响,是浙江几代学者打下的坚实基础。
姜亮夫:海外觅宝不要博士帽
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便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珍贵文献资料。1924年,我国著名学者陈垣在整理被挑剩的敦煌文献资料时曾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34年,刚度过33岁生日的姜亮夫,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的职务,攥着教书积攒下来的钱,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去攻取博士学位。
到了巴黎,参观了当地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后,姜亮夫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国那么多的文物珍宝居然都在国外!当时,受教育等部门委派正在巴黎考察的两位年轻人王重民、向达已在计划将这里的敦煌卷子抄写、影印下来,带回祖国。姜亮夫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
此后,姜亮夫每天一早就进了巴黎的国民图书馆写本部,抄录敦煌文献,对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当时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照几张,他在巴黎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
听说伦敦、罗马、柏林等地也有敦煌卷子,姜亮夫也赶过去抄写、拍照。阅览了6000余份敦煌卷子,收集了许多敦煌文献后,1937年7月,姜亮夫回到祖国,开始整理、研究带回来的珍贵资料。但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写好的《瀛涯敦煌韵辑》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因战乱而遗失;从海外带回的珍贵资料,除300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幸存外,其余均毁于侵略者的炮火。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姜亮夫的满腔爱国热情,才得以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先后发表了《敦煌———伟大的宝藏》、《瀛涯敦煌韵辑》等敦煌学大著。同时,他还长期在浙江教书育人。
“十年动乱”时期,敦煌学的科研和教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后,便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流言,于是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联名呼吁:必须注重敦煌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后,80多岁高龄的姜亮夫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杭州主持开办敦煌学讲习班。讲习班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位有讲师职称的教师。同时,他又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敦煌学新作。
姜亮夫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以自己的行动和著作证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蒋礼鸿:毕生为敦煌打造“天梯”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谜团:“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但是,当人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了唐、五代时的“变文”(民间说唱文学)后,才弄清了这些问题。因此,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但是,要读懂变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7年,王重民、向达等6位学者将海外抄写来的、国内收藏的敦煌变文资料经整理后,结集出版了一本《敦煌变文集》。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变文都是人工抄写的,所以文中有不少是当时常用的俗字、别字,如将“肉”写成为“ 字”,今天,面对这样的奇怪字体,人们自然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敦煌变文中还有大量的民间口语词,由于朝代的更迭、时间的久远,今天,人们也很难理解这些口语词。
敦煌变文难读,当不少读者发出这一感慨时,浙江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开始着手打造“天梯”。凭着深厚的古汉语功力,用了两年时间,蒋礼鸿先生读完了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同时,一本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也问世了。
浙大博士生导师黄金贵说:“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于1959年。当时,这本书的纸张之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有些‘草纸’的质量也超过了它。这本书只有薄薄的80多页,5.7万字。但是,就是这样的纸张,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日本著名的汉语俗语研究学者波多野太郎就指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以说是大著。裨益中外学者很大。”美国学者则誉之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更认为:只有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的书多了,我们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
这本小书何以获得如此评价?蒋礼鸿的学生褚良才博士说,蒋先生在书中阐释这些疑难字词时,引用的古书多达100多种,包括900卷的《全唐诗》、500卷的《太平广记》、100卷的《法苑珠林》等大型古代典籍,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民谣、佛经、道书、诏令、奏折、韵书、史传、文集等,无一不在采摭之列。所以,这本书后来也就有了“撼山易,撼《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结论难”的美誉。
此后,蒋礼鸿先生的研究目光长期锁定在古代俗语词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不断得到充实,1997年,该书出第六版时,字数已由初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5.7万字增至43.6万字。今天,《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早已成为敦煌文献研究者人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所有敦煌学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书。这座“天梯”引导着中外许多学者步入敦煌宝库。蒋礼鸿为敦煌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郭在贻: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科研、教学队伍青黄不接,人才结构呈“倒三角”现象,即老一辈学者的人数还有不少,中年学者较少,青年学者奇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年的杭州大学冒出了一个中青年大学者,他就是郭在贻。
郭是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文革”前已留校任教。他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阅资料室的藏书。“文革”开始那年,他已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进入到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10年动乱,他专心读书、研究。其间,闹出的最大笑话是:一次,郭在贻去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看书,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飞逝,猛一抬头,发现肉店已关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处,而家中还在等着他买的肉。
“文革”结束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敦煌学的研究,浙江很快成了研究敦煌学的热地。郭在贻凭借深厚的古文献和古汉语功力,转入古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先后发表有关敦煌文献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指出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存在许多错误。郭在贻便提出,用学校新购买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来对照《敦煌变文集》,并制订了撰写“敦煌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典》)的计划。他带着学生一起搞这一宏大的项目,在科研中锤炼学生。1989年,已是博士生导师的郭在贻英年早逝,但是《〈敦煌变文集〉校议》已经完稿。以后,他的学生又完成了《敦煌变文校注》等不少力作,并由此跻身国内知名学者行列。
郭在贻的“敦煌三书”计划培养了几位杰出的年轻学者,同时,勤奋成材的郭在贻也成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学习榜样。浙江敦煌学从此出现许多年轻学者,浙江也成了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所以有人说:“郭在贻是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籍学者柴剑虹教授说:“敦煌学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今天,站在新平台上的浙江敦煌学一直在夯筑不断提高的基础。继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设敦煌学课后,浙大也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敦煌学选修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理工科的学生也选修了这门课。褚良才说:“浙江敦煌学以语言文字的成就享誉海内外,此外,浙江学者史岩、王伯敏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敦煌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法律、建筑、医学等方方面面,内容相当丰富。浙江敦煌学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就需要有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要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同时,前辈学者在开创敦煌学时,形成的热爱祖国、执着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敦煌精神’也应该让广大学生了解和继承。” (张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