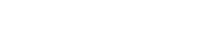到今年8月,谭其骧先生逝世已整整10年了。他病重期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选入该所出版的《500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这是该所为庆祝成立25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世界性名人录,收录已往四分之一世纪间“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精英,即富有想象力、智慧和社会责任感的领袖人物”。谭先生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
我认识谭先生,是1947年秋季在上海暨南大学。那时他在浙江大学任教,由于物价飞涨,教授薪水微薄,他不得不到暨大兼课,多拿一份薪水。当时暨大名师荟萃,单说文学院,中文系有刘大杰、施蛰存;外文系有孙贵定、钱钟书、李健吾;历史系有顾廷龙、沈铼之;教育系有刘佛年……谭先生每次来上课,都是穿一件蓝布大褂,戴褐框眼镜,把布包往讲台一放,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他讲的中国沿革地理和魏晋南北朝史,都是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又旁征博引,颇能引人入胜。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更可贵的是,他每周两次风尘仆仆于沪杭之间,常常不能稍事休息就走进课堂,但他始终神采奕奕,认真教书,这给同学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和异常的好感。
有一次,我偶然翻阅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谭先生的文章《新莽职方考》赫然入目。这部历史文献编入的都是历代著名史学家的杰作,如清朝的万斯同、钱大昕等。谭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大概只有20多岁,他的文章就和这些大师们并列,这使我对他更加崇敬。后来我们知道,谭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生中是佼佼者,很受顾颉刚、邓之诚先生的器重,20岁刚出头,就登上燕京、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大学的讲台,并协助顾先生主编历史地理学的权威杂志《禹贡》。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中,他早已成就很大,名气也很大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复旦历史系派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向系主任周予同先生建议聘请谭先生到复旦任教。周先生接受这个建议,向谭先生发了聘书。可能是办手续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毕业以后,谭先生才到复旦来。
1953年4月3日,复旦历史系部分师生到苏州吴宫遗址考察,两千多年前的吴宫,连断垣残壁也已荡然无存,荒野中只散落有一些碎瓦片。因为年代久远,这些瓦片甚至比秦砖汉瓦更加宝贵。这天到苏州来的除同学外,老师有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胡厚宣先生和师母桂琼瑛,马长寿先生,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古代史助教邓廷爵。顾老先生精神奕奕,谈锋甚健,一边指导寻找瓦片,一边“摆龙门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吹牛皮”和“拍马屁”这两个词都发源自西北,兰州一带黄河水流湍急,用木船摆渡船常常被碰坏,当地人用整只羊的皮晒干漆上油漆,吹上气使它鼓起来,十来个这样的羊皮排列三行扎在木棍上,上面就能坐五六人,用这种羊皮筏渡河既轻便又安全。羊皮可以用人力吹气,牛皮那么大,人力是吹不起来的,如果有人说他会吹牛皮,就会被讥为说大话。“吹牛皮”就成了说大话的代名词。西北人养马的很多,有钱人往往养了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有人为了讨好马主人,往往拍拍马屁股对马赞不绝口。“拍马屁”就成了讨好人的代名词。大家听了感到很新鲜。
当时我的妻子周明绮在苏州一所中学教书,她是我在复旦的同班同学,这一天是我们的孩子陈小川周岁生日,我从上海回家。我和周明绮商量,请老师们来吃饭,她很赞成。我对谭先生表示,他没有推辞,很实在地说:你去准备,我来打招呼。当天中午,来了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胡厚宣先生夫妇以及邓廷爵。马长寿先生大概因为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互不认识,没有来。其实顾先生也是我们毕业后才到复旦来的,也没教过我们,但和我们有点因缘,我和周明绮结婚时,同学黄永年(陕西师大教授、唐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请顾先生写了一幅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送我们作礼物,顾先生大概早已忘了。谭、胡两先生都出自顾先生门下,我们则是再传弟子,有这么一层关系,顾先生也就毋须客气了。
我们招待这么尊贵的客人,却是极普通的饭菜,没有一样是美味佳肴。家具更是寒酸得可怜,桌子是农村那种四方桌,没有一张像样的椅子,大家坐条凳。客人都极不寻常,顾先生是史学界泰斗,名满天下。胡先生是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当时同学中就流传说:“四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不如一宣”,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也可说明胡先生造诣之深。后来出版的集甲古文之大成的《甲古文合集》,名义上主编是郭沫若,据说胡先生出力最多。谭先生则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由于师生关系密切,也由于解放初期风气淳朴,他们才肯来吃这顿不像样的饭。若干年后我和周明绮谈起此事,都感到我们当年的举动近似荒唐。
1956年,谭先生来北京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历时10年才完成。他住在东四附近一个招待所里,我去拜访他。他时间宝贵,我坐了一会儿想告辞了,他留我多坐一会儿。他没有说编绘这部地图集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务,只简单谈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谭先生说,胡同口有一家叫“四如春”的湖南馆子,清蒸甲鱼做得很好。吃过饭我要付账,我说,您到北京,我应尽地主之谊。他说,你来看我,地主是我。结果还是他做的东。
60年代初,我凡出差到上海,或谭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我有机会就去拜访他。
1977年,谭先生访问罗马尼亚回到北京,住在前门饭店。他知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报社就在前门饭店对面。有一天下午他到报社看我,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彼此倍感亲切。他兴致很高,谈了“四人帮”在上海的肆虐,复旦师友的情况,大约谈了两小时左右。我们谈话时门是开着的,光明日报编辑史美圣看见了,第二天对我说,谭其骧这样的名教授居然来看你这个学生。我说,谭先生没有架子,对待学生像对待朋友一样。
1981年,我主持编纂《中国史学家评传》,评介孔子以后中国80多位最著名的史学家,其中一篇评介顾祖禹及其《读史方舆纪要》,这篇文章谭先生写最合适,我写信向他约稿。据说谭先生不喜欢别人出题目、定时间请他写文章,但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中国史学家评传》由周谷城先生署检,白寿彝先生作序,又有谭先生等多位著名史学家撰文,使得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香港文汇报都发表评介文章,赞扬该书的学术价值。台湾还来购买繁体字本的版权。
80年代初,收到谭先生一封信,是由他的女儿代笔的,因为他患脑血栓后手脚不灵便了。信上谈到他主编《历史地理》杂志(副主编为侯仁之、史念海),希望光明日报发表一篇介绍文章,以扩大影响。我当然要尽力帮忙。后来文章由谭先生的研究生葛剑雄寄给我。据说葛先生是中国授予的第一个文科博士,这也是谭先生的光彩,我很为先生高兴。
此后我到上海,都去拜访谭先生,他已从复旦搬出,住在淮海路一座公寓里,看到他行动不便,我心情颇为沉重。
1992年8月谭先生去世,我正在福建老家,消息不灵,我竟没有发一封唁电。后来看到旧报纸,知道他去世后遗体覆盖着写有“华夏文化”的白布——华夏文化代表人之一,先生当之无愧。(陈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