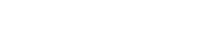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洲大陆的东南方,与南极洲隔海相望,被称为“世界之尽头”。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之一,有40%的面积被列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或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1870年10月15日当地一份称为“Examiner”的报纸,刊登一则题为“从维多利亚来的中国人”消息。报道以温和的口气叙述了第一批19位中国人的到来,但显然带着欧洲人的偏见评述这批华人的到来对岛上社会文化的长远影响。时间过去了近150年,2012年6月21日,就在同一份报纸上,刊出一则新闻:“中国学者盛赞关帝庙”,报道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代表团来考察一百多年前华人留下来的遗产和记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也同时做了报道。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代表团一行四人,得到澳方资助,应塔斯马尼亚大学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心邀请,于2012年
“锡龙踪迹”
“锡龙踪迹”是由当地学者和政府经过十多年的挖掘和研究,将原来锡矿矿区的多个文化遗址、村落、故道和博物馆设计成一条以中国龙为主题的休闲旅游线路,而每个观光点从不同角度展示塔斯马尼亚岛早期华人开拓者留下来的遗迹、生活记忆以及自然风光。出乎我们意外的是,现在这里已经鲜有华人居住,整个路线都是欧洲后裔对一百多年前华人遗迹的展示、解读和想象。
6月22日,在当地政府安排下,由旅游局官员带队,在当地博物馆研究室主任,以及塔斯马尼亚大学和悉尼大学教授等陪同下,我们从Launceston出发到达Branxholm。下车后,迎接我们的是一个两人多高的以龙为背景的高大纪念亭“锡龙踪迹”(Tin dragon‘Trail Marker’)。以大红色为主调的亭子衬托在田园般的乡村风光里,看起来格外耀眼。据旅游局官员说,这样的亭子沿路不同景点都有。是因为我们的到访,昨天才刚刚安置到现场的,我们顿觉一股暖流。当地八十多岁的Auton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爷爷的故事。在一百多年前,他爷爷带着儿子们,从Hobart徒步走到这个地方,成为最早的锡矿开采者。他带我们参观了当年一位名叫Ah Moy的华人矿工家的遗址,Ah Moy家有华人经常聚集的小卖部,如今只剩下一堆据说是搭烟囱的石块。Auton老先生还给我们看了他保留下来的一些华人照片和当年报纸。他告诉我们,这里的华人离开后都不再回来,只有Ah Moy的后代Bill Moy在1983年,也就是这个小镇建立一百周年的时候回到这里。翻开1983年的杂志,里面有一篇针对他回访的图文并茂的报道。当时,这位华人的回访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据说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当地欧洲后裔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挖掘华人踪迹文化的工程。
沿着山路驱车不久,我们就到了Briesis水渠的遗址。这是一百多年前大型锡矿开采公司Briesis修建的水渠。水渠共48英里长, 从Ringarooma峡谷开始,流经Branxholm,止于Derby的矿区,可以想象当年华工投入的巨大人力。现在其中一段水渠遗址开辟为供游客在森林里徒步的小道(walking track)。这一段路掩映在茂密的桉树林间,蕨类植物覆盖着当年人工修筑的石头水渠,往纵深走会出现一个个小瀑布,潺潺流水声不绝于耳。爬上一个小坡,就看到了如今已经破败的木头搭造的引水槽横跨在山谷中。
走出山谷,我们继续驾车到Derby小镇,这里建有一处“锡龙解读中心”(Interpretation Centre)。这是一个环形多媒体博物馆。气势磅礴的影片介绍了这个锡矿鼎盛时期的景象,生产流程,以及修建水渠和大坝的宏伟景观。影片的高潮是1929年发洪水导致大坝崩塌的景象。洪水将整个村庄和矿区淹没,造成了巨大生态与生命灾难。许多华工也因此丧身。
走出放映室是一处十几米的艺术长廊。整个长廊是以老子《道德经》为主题。各种巨幅图片配有中英文的老子格言,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这些图片似乎说明两大主题: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华人“上善若水”的精神 --- 他们面对艰难环境、忍辱负重、与世无争、但又义之所向,无所不克。走出博物馆,极目远眺,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发洪水的整个自然景观。这个博物馆把实景、现代动画模拟、艺术展示、哲理解读融为一体,很有创意。市政厅还给我们提供丰盛的午餐。可能是政府的精心安排,我们每到一处,都有咖啡,当地知情人和各种资料安排,让人感受到那种中国地方官员陪同外国友人热忱和周到。
吃完中饭我们散步到Derby School Museum。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几位工作人员马上迎上来给我们介绍这个学校。据说Derby School于1897建校,到1909年有两百个学生,他们都是Derby锡矿矿工的孩子,其中不少是中国人的子女。这里展览了当年学生们的照片,教室的一些用具,比如黑板、打字机、煤油灯,农具等。当年课桌椅也还基本原样摆设在那里,其中还展示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文物。
离Derby不远有一处叫Chinese Memorial的公墓。其实公墓里绝大部分葬的是欧洲移民,只有很少几个华人坟墓。公墓边一块牌子介绍说,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去世后都把尸骨运回祖国。尽管当时塔斯马尼亚不禁止中国妇女移民,但这里绝大部分矿工却都是单身。他们活着没有把这里看做是家,死了也非要叶落归根。在公墓里我们看到一处华人墓,大理石墓碑上面刻有“大清国大伯公坟墓:光绪三十二年”。墓边上有一个水泥筑成的炉子,上面套着一个看上去怪怪的烟囱,据说这是祭坟烧纸钱用的。当地白人如今写了很多关于华人的记忆,当年不断放在坟边的蜡烛、纸钱以及中国食物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葬礼风俗。
接下来,我们的车队前往Weldborough。据报道说,一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里还是这岛上中国文化的中心。Weldborough、Galdstone、Morrina 是当时以华人为主的三个村落,而Garibaldi则是清一色的华人村落。我们在Weldborough的一条公路边的营地停车,这是一处景观优美的开阔草坪,陪同我们的博物馆策展主任告诉我们这里就是现在安置在Lanceston Royal Park博物馆的关帝庙原址。关帝庙当时被西方人称为“The Chinese Joss House”。矿区鼎盛时有华人1400多。1880年5月Examiner报纸上说:“目前整个区内10个中国人比1个欧洲人,每天还有源源不断的新来者。”当时区内据说有3处关帝庙。但到1921年塔斯马尼亚岛已经只剩下234华人,他们以蔬菜种植和一些小生意为生。到1930年在Weldborough关帝庙最后守护人Hee Jarm已无法继续呆下去,于是把庙捐给Launceston博物馆。还留下来的华人给Hee Jarm捐款,使他有路费得以返回中国故乡。整个关帝庙及其文物自那时起一直保存至今,即使在中国也已经看不到如此古色古香,地地道道的关帝庙了。现在这个营地已经空空如也,但当地白人还在讲述昔日中国矿工围绕关帝庙的生活场景:唱戏、麻将、孔明灯、还有节日里的舞龙舞狮。
Blue Tier是一片山区高原,自然景色无疑是整个路线中最美的。极目远眺、群山逶迤,周边是茂密森林,山上是低矮的耐寒植物,点缀着澳洲特有的巨型石块。车队沿着山路盘旋而上,在快到山顶的地方就是当年Poimena 村庄的遗址。据说欧洲人嫌这块山区环境恶劣离开了,所以后来就成了中国人的村庄。St Helens的历史展馆介绍说这个村庄的设施曾经很完善,有旅馆、诊所、医院、教堂和面包店等等还有自己的学校。但如今看去人留下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只有那些高大的松树还见证着当年的华人的沧桑。
“锡龙踪迹”的最后一站,也就是龙尾是在St Helens,那里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展示更多的华人文物,其中有St Helens地区从1898到1905年间矿主们申请开矿的政府登记薄。博物馆特别展示了当年华人中最有影响的Maa Mon Chin(马文振)家族照片。马文振几乎成为整个华人社区的代言人,深受当地白人的尊重。他也是少有的几个带着眷属的华人。展览馆讲述了Maa Mon Chin夫人16岁嫁给40岁的马文振。她于1881年,带着一个丫环由George Bay登陆,两个缠了小脚的女人在非常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25英里才终于来到Weldborough。史料还记载了她拥有中国淑女的形象,受到当地人的仰慕。她以女人角色关怀华人矿工,在矿区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20年里,她为马家育有7个儿子,4个女儿。
华人离开后,欧洲人对留下来的文化遗迹想象有时甚至到了一种浪漫的程度。三十年代电影明星梅尔·奥碧(Merle Oberon),曾一度被包装为塔斯马尼亚华人的“名门之秀”,认为是华人Chintock家族的女儿Lottie Chintock(1886-1951)在她少女时代在St Helens酒店打工期间和酒店老板John Wills怀上的私生子。其实梅尔·奥碧并没有任何中国的血统,但有意思的是她故意模糊自己出生,还专门登上塔斯马尼亚岛为这个传说背书。直至梅尔·奥碧去世的时候还都被冠以“最有名的中国裔塔斯马尼亚人”的称号。
中国矿工是塔斯马尼亚岛东北部最早的开拓者,为当地经济、社会福利、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曾为Lanceston医院捐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款。因此华人开拓史已成为塔斯马尼亚岛的重要历史部分。当地人对这些“人去楼空”的华人遗迹的保护和研究更多地是处于对这一历史的怀念。最近几年这些遗产又成为推动当地休闲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他山之石”
“锡龙踪迹”是一个建立在西方遗产观,完全由欧洲人挖掘、想象和主导的中国文化遗产。西方学者对视觉艺术、文化记忆以及文物原真性的追求,还有他们对休闲和旅游的特有理解均为“锡龙踪迹打上了独特的跨文化印迹。他们对历史遗迹的高度重视,以及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资源都是非常值得国内遗产界学习的。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是一个缺乏中国人声音的遗产展示,尤其是当触及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时,西方人似乎仍然在云里雾里。也正是这个原因,塔斯马尼亚大学邀请浙江大学学者展开合作研究。关长龙教授有关关帝庙信仰的公共演讲,吸引了当地重要人物以及澳大利亚媒体的广泛关注。他们目前最关心的是,那些当年回到祖国的华人矿工及其后裔在哪里?他们后来的生活和命运又怎样?今天,在中国还有多少有关这些矿工在塔斯马尼亚的记忆?澳大利亚学术界对与中国大学合作展开这些问题的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
塔斯马尼亚大学一年一度的有关文化遗产的冬季论坛,今年的重点就放在与中国的交流上,吸引了澳大利亚从事华人文化研究的学者。冬季论坛专门开辟“文化遗产解读”的分会主题,由浙江大学三位学者主导,深入探讨中国文化遗产观。跨文化研究所所长吴宗杰教授带去了“物质与精神遗产界限的模糊化:衢州水亭门遗产研究项目”的学术报告。他以近期的文化遗产研究为案例展现了他对代表原真性、物质性、纪念碑性的西方“遗产话语”的解构和批判,从中国地方志和经典里解读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不同认识和利用方式。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讨论;关长龙教授的“礼典与展示的象征边界:中华传统礼器漫说”的学术报告与大家分享了中国传统礼器的界定、类别和使用的情况。他从文物的生活情境,当代展示方式,以及礼器背后的文化大义,发表了中国古代对礼器的独特见解;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外籍专家Jeffrey Moser博士向与会者介绍了“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建馆理念及文物收集情况。他代表浙江大学邀请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今后一起参与浙江大学博物馆的建设和策展。他生动的演讲,以及呈现出来的浙大博物馆愿景让与会学者为之深深打动。浙江大学三位学者从各自不同学科呈现了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的成果,体现了跨文化、跨学科合作的特色和优势。
澳大利亚邀请方还专门安排了浙大代表团走访了塔斯马尼亚全岛重要的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遗址以及自然风光。塔斯马尼亚大学Mitchell Rolls教授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Haiqing Yu博士全程陪同,每到一处还有当地相关学者和工作人员的详细介绍,其热忱和细致让代表团充分体验到澳方对跨国合作强烈意向以及对中国的友谊。
代表团离澳前日,专门与澳大利亚邀请方探讨了今后学术合作的各种可能性。双方计划明年(2013)在浙大召开“他山之石”的文化遗产研究国际会议。会议将突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特色。大家希望借此会议把双方期待开展的一系列合作课题推向纵深。
(温艳)2012-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