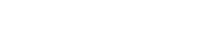霍金访华受到了明星一般的礼遇,图为霍金在游览河坊街时接受杭州女孩的热情一吻
编者按:在一本霍金传记的开头,我们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关于霍金的一切都是新闻。2002年8月9日霍金到达中国之后,新闻界对于霍金进行了巨细无遗的报道。追“星”这样的事情出现在娱乐界早已见怪不怪,而出现在一名科学家身上似乎才真正构成了一个现象。但不管怎样,霍金的中国之行留下了一些值得品味的东西。为此,我们约请霍金教授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博士吴忠超先生撰写此文,详述霍金在杭州的行程和活动,以为一份历史记录。
史蒂芬·霍金预定出席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并于8月9日上午抵达上海浦东机场,由此转道杭州。在茫茫人海之中,接待单位浙江大学通过湖南科技出版社和浙江日报社找到我,受人之托并作为霍金的弟子,我推迟个人的出国行程,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接待霍金教授及公众演讲、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工作。
踏上中国的土地
为了取得霍金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刻的历史镜头,文汇报驻杭记者万润龙和周学忠两位先生找到我,并委托上海的郑蔚帮助我取得进入停机坪的特许证。他们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日上午9时,我和周学忠、郑蔚二位先生来到机场。这时,国际到达出口已经挤满了京沪杭等地赶来的记者。我们被告知飞机晚点2小时,郑蔚先生就带我们去一僻静处喝茶等待。
中午12点多,飞机平稳着陆。旅客散去后,我们几人沿着旋梯走进舱口,只见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正在将一些金属部件铺陈在机旋连接处,我估计那是霍金的助手正在安装轮椅。五年前,我重访剑桥,那时的助手名为汤姆·肯达尔,而眼前的这位可能是尼尔·希勒。我们虽通过电子邮件,却从未谋面。我就走上前去问道:“你是尼尔吗?”他回答:“是的。啊,你肯定是吴,史蒂芬很快会出来。”不久,一位身材颇为高大的褐发妇人步出机舱,她正是霍金夫人伊莱恩。她认出了我,一面和我握手问侯,一面说:“昨夜从伦敦起飞时,就晚点两个小时,让你们久等了,很抱歉。”我说“你们一行飞了十几个小时,十分辛苦。接到你们,我们十分高兴。”
不一会儿,两名护士将全身瘫痪的霍金抱放在轮椅上。漫长旅途后的霍金显得非常的疲惫。这是我五年后再次见到他,心头仍然不免感到震撼,更不用说那些初次见到此场景的人们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史蒂芬,欢迎你到中国来。”霍金神态寂寥,似乎还未从遥远的空间中醒来。此时,伊莱恩立即捉住我手,将我手放在他的手上。他的手很温和,并不僵硬,我想这就算我们握过手了。紧接着,我将东道主浙大和浙江政府驻沪代表一一介绍,霍金的嘴唇动了一动,以他力所能及的方式,表示了高兴和礼貌。
霍金独自驱动轮椅向机场出口驶去。我们紧随其后,经过长途飞行之后,他不需要任何人的辅助,体现了挑战命运的意志力。
当他行进在通道上时,二名机场的警卫人员对他摄像。这也是在电视上播出的霍金踏上中国土地那一瞬间的宝贵镜头。
出口处,记者们挤成一团,快门之声不绝于耳,无数闪光灯若雨点般地打在霍金身上,对那些抢在他轮椅之前的记者,他似乎早已司空见惯,听之任之。
候机大厅外,早有专用的残疾人面包车等候。霍金来华前早已将轮椅尺寸传了过来,可是这辆面包车是浙江省唯一能够找到的残疾人用车。不出所料,我们必须将轮椅上的枕头取下,再仰起轮椅,才能将人带椅一并挤入。
面包车的后部,坐着霍金、伊莱恩、尼尔和3名护士,这3名护士轮班24小时护理他。我们与央视记者谭彦姝和梅子坐在车子的前部。开车的女司机身板挺直,戴着白手套的双手紧握方向盘,俨然在执行一项非常任务。
我们的计划是首先前往虹桥机场的国航宾馆,在那儿,霍金稍事休息并做必要的护理之后,再前往杭州。车子开出不久,过一个关口处,突然被拦住,司机紧急煞车。所有的人都立即回首询问霍金是否无恙,因为他的头部几乎顶在车顶。还好,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刚才的紧急情况,仍然是那么寂寞地凝视着前方。为防意外碰撞,在此后的路途中,一名护士始终以手护住他的前额。
原定在国航宾馆停留1小时,实际上,我们停留了整整4个小时。其间,我们便和霍金的随行人员熟悉起来。离开宾馆前,霍金的精神好了一些,他以语音合成器向经理致谢,这是他踏上中国土地上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再次上车,这次是由他的夫人怀抱着他坐在后排。车窗外已是万家灯火,沿途的车灯路灯,透过车窗映照在霍金的脸上,凭借着这模糊的灯光,他面前的护士展开写有26个彩色字母的硬纸板,霍金利用脸部肌肉的些微动作,挑出字母,再拼成词句,这就是他近20年来,除了以轮椅上的语音合成器之外的唯一的交流和表达方式。
隔着过道,我和伊莱恩闲谈。事实上,我和这位霍金夫人并不很熟悉,5年前,我仅在她丈夫的办公室里见过一面。在求学期间,我对霍金的前任夫人简了解得更多一些。
在夫人怀抱里的霍金听着我们的谈话,以脸部表情做着情绪上的参与。车过上海浙江交界,在前面开道的上海警车鸣笛而去,我对霍金说这是向你致告别礼,霍金孩子般地笑开了,他大概觉得很有趣。很早以来,我就注意到,沮丧和孩子般的笑容交替在霍金的面部出现,这两种表情似乎是霍金情绪上最主要的起伏和波动。孩子般纯净的笑容是没有经过世俗社会污染的容颜,而沮丧是对禁锢的无奈和对自由的渴望,毕竟只有灵魂能够自由地遨游宇宙是远远不够的。
雨中,在浙大警车的引领下,车子加速行进。大家都说车子开得快了,霍金听着大家的议论,也兴奋起来。我告诉他们杭州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具有2000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他将入住的香格里拉饭店,在房间里即可俯瞰西湖风景。伊莱恩说霍金的父母1966年曾游历杭州,并带回一幅织锦保存至今,所以霍金对杭州有一份特殊的渴望之情。17年前,霍金首次来华,只到了北京和合肥。在那次旅行后,他患上严重的肺炎,因此不得不切开气管,至今他的喉头还留有当年手术的洞。1997年我再次见到他时,他还询问过合肥的情况,并曾表示希望再次来中国访问。
车过海宁境内,在得知当夜7点新闻联播还未发霍金到达的消息后,一位摄像师立即在此下车,以便将录像尽快传去。此时中雨转成小雨,离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了。
在沥沥细雨中,我们驶进杭州。得知100多位记者已将香格里拉饭店东楼前门团团围住,霍金夫人当机立断,决定从后门进入。车子一停稳,一群侍者撑起大伞为我们挡雨,冷雨顺着伞沿滴在霍金的脸上。虽然当时没有一位记者在场,可是第二天的《都市快报》上还是刊出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的场景。后来我打听到,是记者用非常好的相机,从远处拍摄的。
霍金入住的房间房号为631,是正对西湖的套间。互道晚安之后,大家旋即离去,让客人们好好休息。
面对媒体
次日清晨,依旧是阴雨绵绵。伊莱恩、尼尔和护士们都因为时差,直到下午还高卧不起。霍金本人反而不受时差影响,自己驱动轮椅,来到饭店平台的走廊,在树海之上,欣赏西湖空濛的水光山色。
8月11日下午,尼尔打来电话说,霍金和他正在准备记者招待会,很可能无法在5时之前将“答记者问”准备完毕。霍金要求我届时坐在他身旁,把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文字直接翻译成中文。
大约在霍金访华之前十几天,中方已经将各媒体提的问题传到剑桥。我是在探亲回到杭州以后,才看到这些问题。这十来个问题中的两个,我本人感到不妥,不过既然已经传给了霍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记者招待会是在香格里拉饭店二楼举行。事先,我们观看了会场,熟悉一下场景。4点半刚过,记者已经挤满了会议厅,大约有40多家媒体。5时整,我们从6楼接霍金下来。许多记者是第一次见到他,于是在机场上被媒体围观的场面又再度重演。
招待会由丘成桐先生主持,我坐在霍金的轮椅旁,看着轮椅上屏幕上的文字作即席翻译。浙大的徐有智将我们三人介绍完毕,招待会就正式开始了。
霍金首先在屏幕上打出“你们听得见吗?”语音合成器以温和的男中音问记者,记者齐声答道:“听得见。”我又见屏幕上打出:“我不回答问题7和问题9。”这句话是对我一个人讲的,所以语音合成器并没有播出。我将此意传达给丘先生,丘先生朗声宣布了这一决定,而不回答的部分也正是几天前我认为不妥当的两个问题。于是原有的10个问题,就只剩8个了。
事实上,在限定的时间内,即使霍金预先准备,他最多也只能回答10个问题。如果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现场选词构句,再由机器进行语音合成,我再将此翻成中文,那招待会将会更加冗长。霍金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当他回答问题时,他熟稔地以大拇指选着字,绝不忽略任何一个冠词,造出的每一个句子都力求完美无瑕。有时,从行文中我已能体会其全意,他仍然坚持敲完最后一个标点。一面是霍金的镇定和不苟,一面是媒体之间激烈的竞争,双方互动蔚然成趣。
丘先生先后点了新华社记者张乐、央视一台和四台记者刘振莉和谭彦姝、文汇报记者万润龙和浙江日报记者张冬素等8位记者,他们的问题大致都很得体,然而却没有一个问题是有关霍金研究的。记得其中的一道问题是:“你认为下个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霍金回答:“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他一面说,一面看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笑容,有一种小恶作剧后的得意。回答完8个问题之后,是记者自由提问时间。有记者发问:“对照你1985年来华,中国在这17年里发生了什么变化?”霍金回答:“85年满街自行车,而现在是交通堵塞。”霍金的回答反映了他之所见,因为他从上海浦东到杭州,只见到了这些,还没有看见别的。
每次霍金准备回答即席问题时,都需要十几甚至20分钟,在等待过程中,丘成桐先生就穿插回答一些记者提问,比如霍金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等问题,以解等待之沉闷。
招待会快结束时,台下的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二位代表频频向我使眼色,于是我即对霍金说:“出版你的中文版著作的出版社想向你赠书,以表达中国读者的谢意。”他立即在屏幕上敲出“现在”。我招呼他们上台,伊莱恩代表霍金收下了印刷精美的中文版的《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并请他们与霍金合影。可惜,湖南科技出版社的代表自己没有携带相机,只是让记者们拍了一通。无论如何,他们从长沙赶来,也算是不辱使命。
招待会后,是浙江省省长的晚宴,因为霍金需要进行护理,所以省长及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多等半小时。
次日数学会议正式开始,霍金被安排作第一个一小时的报告,题目为“M-理论的宇宙学”,基于同样的护理要求,他发言也只能推迟至下午。而我则抓紧时间将他的公开演讲《膜的新奇世界》译成中文。12日之后,承蒙浙大厚意,他们邀请我参加每一次官方的正式仪式和宴会,可是我因事务繁忙,尤其不喜官场应酬,也就一一推辞了。
泛舟西湖
8月14日上午,伊莱恩通知我下午2时大家一起去游西湖,5时去逛河坊街,当晚8时霍金邀请丘成桐、我和王立人三位去香格里拉的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
我们下午2时准时来到631号房间。当天上午,似乎霍金和夫人有些小不愉快,所以霍金先到伊莱恩的房间去谈了好一阵子,说服了夫人一道前往。
我们一行人从饭店后门出来,绕到东面,再走到西湖码头。一出后门,霍金夫人即用一把王星记的黑扇遮阳,她笑着对我说:“你送给我的那把檀香扇很宝贵,不能这么用。”我说:“你回剑桥就可以用那把扇子了。”她说:“剑桥可没有这样强烈的阳光,也没这么热,用不上那把漂亮的香扇,我将把它珍藏起来。”
我们所去的码头位于风雨楼之东,距饭店后门不过区区200米,却用了半个小时才到达。原先,霍金打算让大家分乘两条小船,再另派一船专司摄影,由船夫们将这三条船划向三潭映月。可是气象部门告知下午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就都登上画舫这条大船。
霍金夫妇坐在画舫的最前方,船儿缓缓前行。此时,天阴欲雨,山色空氵蒙。孤山、阮公墩和湖心亭渐次后退,城隍山、九曜山、南屏山和玉皇山迭次涌出。一束夕阳映照在雷峰塔顶,在周遭的一片黯淡之中,金顶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丘成桐向霍金夫妇解释道这个塔是在旧有的遗址上新近重建的,并就此讲起白蛇传。
丘先生说,古代有一只白蛇,化作妇人,勾引书生(SCHOLAR)。其实《西湖佳话》中的许仙是一名药店伙计,而在戏文里,他就变成了百无用处的书生。此时,伊莱恩立即接口道:“那白蛇化成的妇人一定很美丽。”大家哈哈大笑。丘先生接着讲:后来法海和尚警告许仙,并告知白蛇真相,懦弱的许仙临危退却。于是,白蛇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最终白蛇不敌,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之下。我说这塔在78年前就已倒塌,可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白蛇。伊莱恩问我你一定知道许多的典故,我答道,是的,但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
谈笑间,不觉已经到了小瀛州和三潭映月附近。我对霍金讲,这三座石灯比剑桥还要古老,它们指示着西湖最深之处。此时,船上有人讲,如果是阴历8月半,这里可以看见15个月亮。丘先生听了马上就说这根本不可能,科学家本色又露峥嵘。
画舫在三潭停留一阵,我们没有上小瀛洲即返回。回程上,霍金夫妇很想看“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景色,可谓正当其时。可惜画舫不能穿过苏堤六桥开往刘庄去,我们只好返回西泠桥下。荷花的美丽脱俗人人喜爱,其实它并非本土所生,而是从印度传进来的,霍金夫妇也陶醉在荷花的氤氲之中。临上岸时,有人从湖上采来三朵荷花,伊莱恩将其放在丈夫鼻下,让他把闻,然后叫人放在他的住房里。
大约5时,霍金一行来到河坊街,计划在“胡庆余堂”附近驱动轮椅行走200米左右。在粉墙黑瓦的衬托下,“胡庆余国药局”几个大字分外引人注目。伊莱恩问其何意。我告诉她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药局。前面是一家茶馆,主人上来敬奉一杯“九九红曲茶”。霍金听了祝词,也弄不清是什么含义,反正客随主便,别人送什么,他就喝什么,只管喝下去。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杭州市民已经在前几天的电视上见过他,他已成为街头巷尾妇孺皆知的人物,人人争睹为荣。这时,途经一处臭豆腐店,他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他此物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是豆腐发霉制成。中国人称西方的乳酪为洋臭豆腐,你就叫它中国的乳酪吧。
霍金来到一家工艺品商店,他对内画壶非常感兴趣。一个年轻人当场为他表演内画。我请他将霍金的名字写在内壁,因为是悬腕,不可能太精细,但已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我告诉他明天会收到一个礼物,鼻烟壶里画有他的彩色画像,比这个好很多。
再往前走,即到达伊莱恩前天定做连衣裙的店铺。店家殷勤地叫了两个小孩给霍金献花,并赠送他一套丝绸睡衣。伊莱恩的连衣裙花色如龙袍,在余下的几天里,她穿了好几次,看来她很喜欢这件衣服。在一家竹艺摊,霍金又收到竹编的蛟龙和鳄鱼各一条。
天色已晚,我们决定不回饭店吃意大利菜,而就近在“钱塘人家”用餐。霍金不能吃素油,只能吃黄油,并且不能吃面粉,店家为他准备了特殊的炒粉。大堂里摆好两张大长几案,上陈时鲜水果四种,霍金的轮椅放在大堂中央,伊莱恩在其右手为他喂食,我坐在左面。随行人员分坐两旁,护士们早已趁空逛夜市去了。
虽然店家使出浑身解数,霍金却只吃眼前几样简单的菜肴。后来人们敬他一杯米酒,酒盛在古香古色的三角樽中,伊莱恩将樽送至他嘴边,一饮而尽,当然大部份都流失在他系着的餐巾上了。他似乎胃口很好,酒后兴致很高,这时我看见他在电脑上打出一行字:“我能解决M-理论了!”他并按动语音合成器,发出酒后豪情。
在杯觥交错之间,我看见他又写道:“在中国,像罗马人那样的行事,mixmetaphors(我猜他想说的是入乡随俗)。”一会儿,他又写道:“85年我首次访华,那时候我并不出名,和这次一样,人们总是围观我,那是因为我坐在轮椅上。”
我不禁对他说:“史蒂芬,85年你已经在学术界非常著名了,《时间简史》的出版使你成为大众人物。”
在如此的热闹之中,坐在轮椅上的霍金备显孤独。回顾其不平凡的一生,他必定百感交集,特别是在这般热闹喧嚣背后,陪伴着他的永远是孤独,这位被锁在轮椅上的“无限空间之王”的孤独一定是超越时空的。
此时,他又在电脑屏幕上打出有关“死亡”的话,可惜我无法理解其意。一般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行文和口述表达都力求简洁,而霍金的情况更使他的交流更为简洁,然而人的感情丰富多样,绝非理性的简洁所能描述,况且人的情绪瞬息万变,当他还来不及表达心有所感时,那些感觉可能早已云消雾散,因为他的表达相当费时,他或许宁愿不说了。当一个人不能即时地与亲友分享喜怒哀乐时,那种寂寞的确是无边的,也的确令人懊丧无比,这是任何荣誉和恭维所不能补偿的。
在2个多小时的用餐中,“钱塘人家”以八面大屏风拦住了围观的民众,胡庆余堂前灯光如昼,人们隔着屏风和警戒线,久久不愿散去。
膜的新奇世界
8月13日中午,我来到浙大数学科学中心,这是丘成桐先生第二次在此建立的中心。此地环境幽静,霍金正在这里午餐休息,我和尼尔约好与他讨论15日公开演讲的细节安排。
我告诉霍金,我已将他的讲稿全部译成中文,目前正在润色。我还对他说:“我觉得比书中的最后一章更为有趣。”这里,我指的是他在演讲稿中对时空维数的最新的激进观点。听到这里,霍金的脸上现出喜色,因为在剑桥,对于一项研究只以有趣与否来裁决。
霍金问我:“你打算如何在演讲过程中表达中文?”我告诉他我准备将我的译稿制成幻灯片,在他演讲中,我同步地将幻灯片播映出来,我不再以中文重述。霍金讲:“体育馆那么大,坐在后排的人看不清幻灯屏幕。”此时尼尔也插嘴道:“体育馆是长方形的,似乎后排距离讲台并不很远。”霍金打断他的话说:“我讲一句英文,吴讲一句中文。”吴姓是以两个字母组成,我看着他的屏幕,在他打出第一句话时,我已经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可是霍金还是不厌其烦地找字造句,将整句话打出来。趁此机会,我又告诉他我将不陪他去北京,就在杭州和他道别了。尼尔说你的中文译稿是否可以让霍金带到北京使用,我说当然可以。最后,霍金还说,因为这个演讲相当费时,所以演讲之后,他不回答任何问题。
浙大在一个月之前就收到了霍金的演讲题目,可是他们经查字典及向北京有关方面询问,都不得其所,于是在演讲票面上只好印上英文原文。后来主办单位在《果壳中的宇宙》的中文译本里找到译名。这个《膜的新奇世界》的译名是我凭空杜撰而来,正如历史上的许多科学术语译名,能否存活只有老天晓得。
8月15日上午,在演讲地浙大体育馆,我和尼尔正在讨论幻灯中的字幕,图片和中文翻译如何同步问题时,霍金就到达了。于是我就出去把他接进来。
据丘成桐先生说霍金演讲的出场费为5万英镑。1997年,我在剑桥住在霍金的护士高德文的家中。高德文女士告诉我,霍金在日本的演讲费更高,因为日本人有钱,而这次霍金在浙大演讲是不收费的,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友好情义。虽然浙大是尊重霍金的,演讲票是免费的,可是在会场外面,一张演讲票仍然被炒到400-500元。许多学生从上海赶来,只凭火车票即让他们进场。
霍金自己驱动轮椅驶上讲台。他的头歪向右侧,这是他一贯的姿态。因为颈部以下无法转动和支撑,他斜倚在轮椅上,仅能以眼光扫视宽大的体育馆。
“我们可能生活在更大空间的一张膜或它的表面上”。霍金以这样一句简短的话开始他的演讲,台下3000听众鸦雀无声。
通过语音合成器,霍金的声音在体育馆的上空回荡,我也尽力以庄重沉稳的声音给予准确的翻译。实际上,从事这种现场翻译并不轻松,更何况无法看到演讲人的嘴形,完全凭借语音合成器的声音来进行口译。
在巨幅宇宙星空背景下,一束光线照亮了他瘦弱的身躯,在红色的天鹅绒上投射出淡淡的影子。“我们自以为生活在4维的空间里,但也许我们不过是高维空间事物的投影,就像闪烁的篝火在洞穴墙壁上的投影,但愿我们遇到的魔鬼也只不过是个影子。”
讲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衬托出台上人的孤独和无奈,因为他根本无法以任何姿态表达对听众的谢意。
虽然我无法看清台下听众的面容,可是我知道他们多为年轻学子。当他们在耄耋之年,不知是否还能回忆起今天的一幕。
一个多小时的演讲进行得很顺利。演讲一结束,伊莱恩马上从前排走上来向我握手道谢。她当然听不懂中文,可是她也沉浸在会场的气氛之中。
这时,我终于找到了机会,得以将浙江电视台赠送的内画鼻烟壶呈给霍金。内画的正面是霍金的彩色画像,后面是《果壳中的宇宙》的插图。伊莱恩让霍金以手握瓶以便记者拍照,并让我把它展示给记者,解释画面含义。这是他在杭州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之一。
16日中午,我赶到刘庄国宾馆。透过水上餐厅的大玻璃窗,伊莱恩向我招手致意,她仍然穿着那件金黄色的连衣裙。
浙大负责接待的人员请我在六套中文译本上签名。我打开其中的一本,只见扉页上已印上了霍金的大拇指印,伊莱恩的说明和致谢。这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纪念。
刘庄濒临西湖,远山晕黛,杨柳拂面,微风和畅,恰似暮春三月。霍金驱动轮椅,沿湖边小道行走100米。随后他们和大家合影留念,告别西湖山水,飞赴北京。
车过钱塘江,我向霍金讲起了钱塘潮奇观,可惜此非其时,但愿下次他们来时可以观赏。但愿,还有下一次。
附录1:霍金北京行程
16日晚,霍金从杭州飞抵北京。
17日上午,出席当天开幕的“北京国际弦理论会议”,并作题为《哥德尔与M理论》的学术报告。
18日下午3时,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作《膜的新奇世界》的公众报告。
19日,接受江泽民主席的会见,建议中国保持和发展重视基础科学的传统。
19日晚,在前门饭店梨园剧场观看京剧《闹天宫》。
21日下午,17年后再次登临长城,并接受了“八达岭长城登城证书”。
22日中午,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回国。
附录2:霍金17年前的中国之行
约翰·格里宾等撰写的霍金传记《斯蒂芬·霍金的科学生涯》记述了霍金首次访华的情形:1984年(应该是1985年),远在第一次草稿(指《时间简史》)完成以前,霍金在中国作了一次讲学旅行。这样的旅行计划即使对一个体格健全的人来说也是够紧张的了,但他在访问期间坚持要求尽可能多地安排活动,他驾驶着轮椅逛长城,看北京的风光,在好几个城市对挤满礼堂的听众发表演说。丹尼斯·夏马说,他相信此次旅行使霍金体力消耗过大,甚至还说这次旅行后不到一年便使霍金在瑞士生了一场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