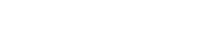在我采访过的著名科学家中,谈家桢算得上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一位了。他坦荡率真,对人有热情,遇事有激情,流露的是真情。所以,在他搬到郊区的养老公寓之前,我经过他陕西南路上的旧居,只要知道他在家和有空,就总要上楼去看看他,因为他是我心目中一位真正的长者。
“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
无论说普通话还是上海话,谈家桢都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因为他的言辞诚恳真挚,所以听起来分外亲切有味。
1991年冬,我们电视传记片摄制组随谈家桢去慈溪寻访他的出生故地。拍摄间歇,我和他一起坐在树下的石栏上休息。他心情愉快地环顾四周,可能是受了故乡景物的触动,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偏不信教;有人批摩尔根我就是不服气,坚持顶到底。”当时,光听语音,我弄不清这小名是不是“倔强”的“强”字,抑或宁波话偕音“祥”字?他说:“不对!是‘倔强’的‘强’字下面再加个‘牛’。”说完还显得很自得。
这使我想起他先前给我讲过的一件往事,正好印证和注解了他的“犟”脾气。
1973年,“文革”时期,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宣称自己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当权的工宣队去问谈家桢相信不相信。问的目的当然不是征求谈家桢的专家意见,而是要逼他这个“资产阶级反动遗传学权威”表态,也就是出面承认和证明那个“培育成功有色棉花”的“农民科学家”的“大无畏革命创举”。不料谈家桢回答:“我没有见过这种彩色棉花。”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对已经被批斗了六年的谈家桢来说,这样的顶撞意味着是在冒怎样的生死风险。可是他还是“犟”了一下。到1975年,已经身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那个“农民科学家”,写了篇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的谈有色棉花的论文,要求和谈家桢联合署名在《植物学报》上发表。谈家桢又“犟”了,说自己没有重复种出过彩色棉花,所以“无功不受禄”,拒绝署名。
他对我说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感慨道:“当时我如果要政治投机,那正是机会。但我是搞科学的,最重要的品德是求真,不能讲假话。我怎么会跟从他们胡闹呢!”
其实,只要浏览一下谈家桢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真可谓是为科学真理和社会正义“犟”了一生的人。
“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
我们每到一地拍摄,总会有谈家桢的许多学生闻讯后不请自来地赶来帮忙。这些学有名声或身有职位的社会中坚,前后张罗联系,周到得恰似大首长的一群警卫员、勤务兵。拍摄的时候,不时会有人急步上去给谈家桢拉拉领子、整整衣襟,甚至具体“指导”他该怎样坐、如何说,直接做起了“现场导演”。有时出现两种不同的“指导”意见,几个人又坚持不让地在他面前争论起来。说实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热情反倒成了我们拍摄的负担。我们只能劝说:“不用了,不用了!”而谈家桢却非常驯顺地随他们摆布,脸上只有像老祖父被儿孙们争着拉扯到各家去吃饭时那种不置可否而又满意喜悦的笑容。最后实在难以取决了,他看看我,慈和地对他们说:“听导演的。”所以,我们一路行来浩浩荡荡,摄像机周围始终人丁兴旺。摄制组的同事都说,这是我们拍片以来从没有过的热闹,也是我们采访科学家时所绝无仅有的体验。
谈家桢真心喜爱这些学生,他对我说:“我这一生没有金钱,财富就是学生。”
这些学生对他当然更是真心爱戴。但只要谈家桢不在场,他们说起话来竟然都直呼他为“谈老头”。好几次,他们正起劲地向我介绍情况,或者商量如何去作拍摄准备时,一声“谈老头”刚刚高亢地呼出,恰好谈家桢走进来了。“叫我有啥事情啊?”谈家桢听力不太好,要靠助听器,常会习惯性地用手去扶一下耳朵。学生们虽然都已人到中年,而这时候就全变得像小孩子似的,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耸耸肩膀、做个怪相,朝他笑笑;而谈家桢则像一位撞破了孩子的调皮又觉得无伤大雅的家长,淡淡一笑,转身慢慢走开了。再接着说下去,他的学生们仍然“肆无忌惮”地直呼“谈老头”,好像刚才的事情全没发生过一样。这真是非常有趣、见了就让人难忘的一幕。
“我和大家一样,是个很普通的人”
应当说,谈家桢是一位非常配合的采访对象,但我却差点儿因为他的热情而闯了大祸。
在作开拍前的准备时,谈家桢为了让我有机会多接触和了解他,有一次邀我陪同他们夫妇一起去常熟访问。我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前座上,到了目的地,赶紧下车准备去搀扶他一下,因为那年他已有84岁高龄了。不料我刚刚随手用力关上车门,未及转身,就听到他痛苦地大叫一声“啊唷——!”我吓了一跳,一看,只见他的两手前伸吊挂着。原来,他因为比较胖,陷在轿车沙发里不易起身,非得用手拉住前面的车门柱才能慢慢跨步出来。我不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前车门一关,就把他的手夹住了!
看到谈家桢痛苦变形的脸,我倒吸一口冷气,吓得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幸有驾驶员迅速打开了前车门。但是,谈家桢右手的四个手指,已经给轧出了一道很深的红色凹印,麻木而不能弯曲了。
还幸亏他夫人邱医生在场,当即做出了诊断:“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那天,要是没有车门边缘上的橡胶密封条做缓冲,谈家桢的右手肯定残废了。虽然如此,手指还是红肿得很厉害,使得谈家桢吃饭做事不便,更不能写字。
我当然自责得不得了,时不时要看他那只手的肿退得怎么样。可是谈家桢总是把手藏起来,不让我看。他说:“你不要紧张,这不是你的错,下车时是要及时关上车门嘛!”回到上海后,我多次打电话去问候和致歉,他也始终是这句话:“这不是你的错呀!”还叮嘱我:“在你同事面前你不要提这件事情。”这使我既为之心慰,更为之深深愧疚。
平时,我碰到的场合,只要听到别人话中有明显恭维的意思,谈家桢总会摆摆手说:“我和你们大家一样,是个很普通的人。”而寻思起来,自己和谈家桢接触次数多了以后,无形中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当做普通人来看待了,心理上没有彼此地位、辈分差别的距离感。
至今我还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从见第一面开始,自己在谈家桢面前就没有任何的拘谨和顾虑,心情特别放松舒畅,而且潜意识里似乎还这样自信:“和他在一起,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功的。”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找不出的原因,我心里分外地敬重谈家桢。
(倪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