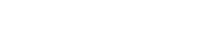初入大学,闻着新教材的油墨香,同时憧憬未来4年的大学生活,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然而,尽管近年来高校教材出版数量快速增长,却有不少教师和学生反映教材质量不断下降,也因此影响了教学效果。
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什么原因造成大学教材质量问题?如何切实提高教材编写和出版的质量?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教师。
差教材影响教学质量
四川某大学教师朱红(化名)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学校教学一线教专业基础课。令她苦恼的是,每学期开课前都会觉得教材比较难选。“很多教材简直是东拉西扯。要是有资金,我都想自己编。每个老师上课都有自己的体系,我希望教材内容也可以按自己的体系来。”
按照学校规定,教师有权选择自己所授课程的教材,如果是几位教师上同一门课,教学秘书就会征求几位教师的意见。然而在朱红看来,尽管有选择教材的权利,却找不到几本值得选的可用教材。
与之相比,山东某大学青年教师许菲(化名)不必为选择教材犹豫不决,却同样面临教材质量不高带来的麻烦。
许菲讲授金融学课程,用的是她所在学校的几位教师合作编写的教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她说,“我参加编写了一本教材,出版社给所有作者5000本书作为稿酬。我们要消化这些书,只能让自己的学生用。”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德广将大学教材分成三类:基础课教材、专业基础课教材和专业课教材。
杨德广认为,基础课教材的选择面应该广一些。目前这类教材编写者比较多,但有些地区或学校为了经济利益、成果产出,尽管教学水平不是很高仍然自编自用教材,而不愿意用最好的教材。“这显然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对于专业基础课教材,杨德广认为可以由某一专业、某一学科有共同特点的学校联合编写,如果各校坚持自行编写,质量也无法保证。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类教材质量确实良莠不齐,“有的比较好,有的不够好”。
至于专业课教材,杨德广认为其涉及内容较窄,应该以一些重点大学的高水平教授编写为主,同时需要不断更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曾指出,一些学校自编教材现象严重。同一门课程有数不清的教材版本,所有的大课、基础课、核心课都有上百种甚至上千种教材,内容大同小异。
据报道,2009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中,从事教材出版的超过60%。出于占领市场的考虑,不少出版社为一些高校出版自编教材,其中大部分都是低水平同质化产品,“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效应使优质产品的生存越来越困难。
好教材是怎样炼成的?
杨德广表示:“我们在教学改革上面,对教材的关注力度还不够,包括教学方法改革,关注的力度也不够。我们提出培养拔尖人才,但拔尖人才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教材培养,这方面我认为还要进一步加强思考和探索。”
杨德广认为教材尤其是专业课教材需要不断更新。早在上海大学主管教学时,杨德广就要求专业课教材每年上课都有所更新,3~5年就全部更新一遍。因为科学技术发展变化比较快,这方面的知识更新也比较快,教材往往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跟进不够,这方面学校应该对教师有所要求,教师应该加强知识的更新,加强自身研究能力的提高,不断更新教材。“我认为应该以各专业的教师为主,不断地更新。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校的专业教师不一定有能力编,但可以借鉴相同类的高校。”
“教材如何做到既有理论又有实际,需要研究。”杨德广认为,我国高校大部分应该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研究型高校不是很多,所以教材编写要强调与实践结合。
“另外,案例要求还不够。让学生去分析、讨论,从分析讨论中上升到理论,教材中如果有些个案,就会生动,学生就会感兴趣。”杨德广说。
“大学教材首先要让学生读得进去。好的教材应该是通俗易懂的。”许菲提到,“我国有的教材拿过来冷冰冰,学生读起来就觉得很烦,感觉是脱离现实的一个框框,没有肉在里头,没有启发学生的思考。”而国外的一些流传比较广的教材会先描述现状然后又有启发思维的练习。“这是‘浅出’的过程。这其实是很难的,要求编著者有自己的想法,才能‘浅出’。”许菲说。
有人在网上发帖对中美教材作了一些比较,其中提到:从详略程度上讲,中国教材有些过于简略,犹如瘦骨嶙峋的乞丐,好久没有讨到饭了,总体上有一种泛泛而谈的感觉,而美国教材体态丰盈,如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优雅而不风骚,又如肌肉发达的运动员,强壮但不野蛮,有血有肉,完整具体,生动活泼。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认为,一本好教材要具备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能从总体上反映课程的知识结构,包括各方面的知识点和拓展的需要;第二,要有助于学生的学习,要将知识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第三,要符合授课的需要,根据教学时数,也就是学分和学时的多少来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张斌贤参与编写的教材比较多,包括北师大教育系原教授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史简编》、北师大教育系原系主任陈孝彬主编的《外国教育管理史》等。最近十年来,他自己组织编写了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史》、“十一五”规划教材《外国教育思想史》,以及最近的“马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教育思想史》等。
其中,《外国教育思想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教材。张斌贤介绍,该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三所学校四位教师一起编写,尽可能地考虑了教学的需要。在这本书之前出过好几本这方面的教材,但大部分更适合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使用。这一本则定位很明确,就是给本科生使用。
张斌贤说:“这本教材不敢说创新,只是尽可能有点变化。这本书从申报教材开始到写出来用了四五年时间,实际动手写花了两三年。至于实际成效会怎样,究竟有多大范围的学生在用这本教材,因为各所学校教学计划不一,确实还不好说。”
小教材背后的“大利益”
“利益关系是教材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的原因。”许菲说,“有些学者、专家编写的教材质量相当不错,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含量。我们在选择教材时,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编写的教材,肯定会选择质量相对有保障的;但如果有我们自己编写的教材,就宁可摒弃一些高质量教材,也要用本校教材,这样,成果也有了,职称也评了。”
许菲认为,教材质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导向出了问题。以前编教材大多会由老教师任主编,请他们根据多年教学经验整合体系。但现在很多人都习惯自己东拼西凑,编教材的目的是积攒成果评职称,而不是精选素材教好课,书的质量当然高不到哪里去;书出版后又想尽办法找销路,坏影响由此四处扩散。
“无论从出版还是作者的角度,当教材是有利可图的,就必然导致教材的泛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表示。
“我们现在主要是编教材太容易了,大家都编,自己掏钱找个出版社买个书号,就可以出。” 别敦荣说,过去我们有统编教材,在保证教材的基本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放开了以后,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编的不能编的都编,再加上有些人比较功利,都去挣科研成果,这就出现了教材鱼龙混杂的情况。还有,教材其实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但不太能够反映学术活动的成就。一本教材应该多人编写才好,但它往往只反映主编的劳动,其他参与者的劳动得不到体现。有些知名学者更倾向于写专著,而不是编教材。这都导致教材编写质量参差不齐。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一直很强调教科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一打著作比不过一本教科书”。葛兆光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认为一流学者不要写教材,认为一流学者写教材是身份的降低,“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认为一流学者要去写教材”。
有人提到,对于教材来说,虽然要有意识地融入学科的前沿观点,但还是偏重于基础性教学,所以对于一些学有专长的学者而言,他们还是不太愿意编写一些基础性的教材。
杨德广表示,一些一流学者不愿意编写教材,这是导向问题。“我国有各种科研成果奖励,但没有什么教材方面的大奖。我认为教材比科研成果要重要多了。科研成果影响某一个方面,但教材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学生来用,应该组织很强力量来编写教材。”
张斌贤也提到,一些教师不重视教材编写,这和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有关系。 “一流学者不编教材”,这是片面的。高校教师在做好科研的同时,决不能忘了自己“教师”的身份。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到教材中,使更多学生受益,这也是一种学术传播。
教材是最难写的书
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材,几乎都是在剑桥、牛津和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校诞生的,国际上广泛使用的物理化学教材,1999年牛津大学再版时,已经是第48版,历年来经过了很多知名学者的修改。
据了解,国际上一些非常杰出的学者都在编写教材,比如经济学领域,国际上流行的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大家在撰写,而国内编写教材的知名学者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
许多人认为写教材是“小儿科”,体现不出学术水平,但杨德广表示,“教材的编写应该是难度最大、水平最高的”。
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办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日前谈到教科书的编写和评价时也表示:这是一项非常具有专业性、学术性的工作。教材的编写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考虑时代背景,又要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
张斌贤分析,目前经典教材难以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高校教师编写教材的热情比过去要高一些,但对于编写一本可能称之为经典教材的投入还不足,追求数量、追求速度而轻视质量。第二,部分教师出于利益动机而不考虑或至少不主要出于质量或适用性的原因选择使用教材,使好教材难以在较大范围使用,从而不利于调动优秀学者编写教材的积极性。第三,我们的教材一旦写完不再修订;有的教材虽然也出修订版,但修订的幅度、程度都很有限。
别敦荣说,一般来讲,一位教师教的科目比较多,不能每门课都自己编教材,势必要使用别人编的教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现实的困难。有的教材过于个性化,有的过于通俗化,还有的相互之间差不多。前些年就有人反映,某一门课的300多本教材基本上是一个模式。这样的教材整体水平必然不高。
近日有媒体报道,教材专著化倾向显著。许菲认为,专著的主观性较强、综合性较弱,在大学阶段学生们正在学习“是什么”的时候,有可能使其立场不够客观、视野趋于狭窄。在她看来,大学阶段的教材内容更应侧重于基础知识,专著则可以作为阅读辅导材料。
别敦荣也认为,教材和专著的性质不一样。教材是为教学服务的,其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本课程的总体框架和基本理论,内容涵盖各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专著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围绕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严格来讲,教材专著化是不合适的。但在教学中,教材和专著应该配合使用,而且应该选用很多专著,与教材相配套使用,才能反映教学的要求。
“关于如何编写教材,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完全在于教师自己把握。当然,很多教材是由编写小组一起合编的。”别敦荣说,“根据我编教材的体会,教材内容的水平和层次要把握适度,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不像专著能写多深就写多深,教材需要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考虑学生的学习领悟能力。”
张斌贤认为,编写教材或专著对不同年龄的大学教师来说情况很不一样,很难说哪个更容易。对新入职和入职几年之内的教师来说,写教材恐怕不是他们擅长的事情。他们更多的应该是围绕某些专题开展研究,也可以尝试写一些选修课的教材。对基础课来说,编写教材需要一定的教学经验,需要对课程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的把握。因为教学与研究不同,研究可以围绕一个专题做得很深,而教材需要完整、充分地反映学科的知识体系,不是说自己擅长的就写很多,其余的少写或不写。
教材要编好,课更要教好
“教材,特别是一些基础课的教材,是引导学生从未知状态进入已知状态的一条便捷途径。”张斌贤说,一本好教材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在某一领域发展的起点高低。
对于学习某一门课的学生而言,有一本好的教材,确实是一件幸事。张斌贤说:“在我了解的非教育类教材中,朱迪斯·贝内特(Judith M. Bennett)和沃伦·霍莱斯特(C. Warren Hollister)合编的《欧洲中世纪简史》就是这样的好教材。我初次阅读这本教材时,就暗自为使用这种教材的学生感到庆幸。”
张斌贤指出,编写一本好教材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难得多:既要考虑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要考虑整个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既要有利于学生学,又要有利于教师教。“这些说起来都很容易,但我现在也不敢说我们编的教材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要求。”
张斌贤认为,教材编得好不好,主要取决于编者对知识、学生和教学的理解。他相信,有了到位的理解,并采用适合学生认知模式的表现方式,是可以编出好教材的。
杨德广认为,教材是为学生提供教学内容的基础,就像电影、电视剧的剧本。教材是教学过程最基本的技术保证,而教学方法是一门艺术。如何把教材内容有效地让学生掌握,称得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艺术。教师是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统领,就像电影、电视剧的导演。教师本身必须有很深的专业知识和学科修养,“导演”不能完全按照 “剧本”,还要自己加工、自己创作。所以大学最根本的还是大师。
许菲也表示,对学生自我的修养来讲,更重要的是教师而非教材。“关键是教师。不同的教师用同样的教材,教学效果会相差很多。教师很差的话,再好的教材也讲不到位。教材有点像提纲,这些课必须学习到这些要点,如果说教师不重要,一人发一本教材去看就好了。”
“现在什么问题都想通过统一的硬性规定来解决是不太现实的。在教材问题上,学术自由以及教师的主动性、个性化都是重要的。”别敦荣认为,关键是应该呼吁教师们在教材的问题上,包括编写教材和使用教材,都要特别严谨。编写教材要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为了职称而编,更不能为了推销给学生赚钱而编。使用教材要充分考虑教学的需要,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别敦荣指出,有的教材水平不高,但教师教学水平高,教学质量也会很高。他说:“教材是‘死’的,真正的教学水平取决于‘活’的人。”
(2011-05-17)
本栏目编辑助理 叶沈俏